体育之研究
国力苶弱,武风不振,民族之体质,日趋轻细。此甚可忧之现象也。提倡之者,不得其本,久而无效。长是不改,弱且加甚。夫命中致远,外部之事,结果之事也。体力充实,内部之事,原因之事也。体不坚实,则见兵而畏之,何有于命中,何有于致远?坚实在于锻炼。锻炼在于自觉。今之提倡者,非不设种种之方法,然而无效者,外力不足以动其心,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。体育果有如何之价值,效果云何,著手何处,皆茫乎如在雾中,其无效亦宜。欲图体育之效,非动其主观,促其对体育之自觉不可。苟自觉矣,则体育之条目,可不言而自知,命中致远之效,亦当不求而自至矣。不佞深感体育之要,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,知海内同志,同此病而相怜者必多。不自惭赧,贡其愚见,以资商榷。所言并非皆己实行,尚多空言理想之处,不敢为欺。倘辱不遗,赐之教诲,所虚心百拜者也。
第一、释体育
自有生民以来,智识有愚闇,无不知自卫其生者。是故西山之薇,饥极必食;井上之李,不容不咽;巢木以为居;皮兽以为衣;盖发乎天能,不知所以然也。然而未精也。有圣人者出,于是乎有礼,饮食起居,皆有节度。故“子之燕居,申申如也,夭夭如也”食饐而餲,鱼馁而肉败,不食“射于矍相之圃,盖观者如墙堵焉”。人体之组成,与群动无不同,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,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。人则以节度制其生,愈降于后而愈明,于是乎有体育。体育者,养生之道也。东西之所明者不一:庄子效法于庖丁,仲尼取资于射御;现今文明诸国,德为最盛,其斗剑之风,播于全国;日本则有武士道,近且因吾国之绪余,造成柔术,觥觥乎可观已。而考其内容,皆先精究生理,详于官体之构造,脉络之运行,何方发达为早,何部较有偏缺,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,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。故其结论,在使身体平均发达。由此言之,体育者,人类自其养生之道,使身体平均发达,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。
第二、体育在吾人之位置
体育一道,配德育与智育,而德智皆寄于体。无体是无德智也。顾知之者或寡矣。或以为重在智识,或曰道德也。夫知识则诚可贵矣,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。顾徒知识之何载乎?道德亦诚可贵矣,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。顾徒道德之何寓乎?体者,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。其载知识也如车,其寓道德也如舍。体者,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。儿童及年入小学,小学之时,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,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。宜以养护为主,而以教授训练为辅。今盖多不知之,故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夭殇者有之矣。中学及中学以上,宜三育并重,今人则多偏于智。中学之年,身体之发育尚未完成,乃今培之者少而倾之者多,发育不将有中止之势乎?吾国学制,课程密如牛毛,虽成年之人,顽强之身,犹莫能举,况未成年者乎?况弱者乎?观其意,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,以困学生,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,有不受者则罚之;智力过人者,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,甘言以恬之,厚赏以诱之。嗟乎,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!学者亦若恶此生之永年,必欲摧折之,以身为殉而不悔。何其梦梦如是也!人独患无身耳,他复何患?求所以善其身者,他事亦随之矣。善其身无过于体育。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。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。于吾人研究之中,宜视为重要之部。“学有本末,事有终始,知所先后,则近道矣。”此之谓也。
第三、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
三育并重,然昔之为学者,详德智而略于体。及其弊也。偻身俯首,纤纤素手,登山则气迫,涉水则足痉。故有颜子而短命,有贾生而早夭,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。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,一旦身不存,德智则从之而隳矣。惟北方之强,任金革死而不厌。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。烈士武臣,多出凉州。清之初世,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。习斋远跋千里之外,学击剑之术于塞北,与勇士角而胜焉。故其言曰:“文武缺一岂道乎?”顾炎武南人也,好居于北,不喜乘船而喜乘马。此数古人者,皆可师者也。
学校既起,采各国之成法,风习稍稍改矣。然办学之人,犹未脱陈旧一流,囿于所习,不能骤变,或少注意及之,亦惟是外面铺张,不揣其本而齐其末。故愚观现今之体育,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。非不有体操课程也,非不有体操教员也,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。非徒无益,又有害焉。教者发令,学者强应,身顺而心违,精神受无量之痛苦,精神苦而身亦苦矣。盖一体操之终,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。饮食不求洁,无机之物、微生之菌,入于体中,化为疾病;室内光线不足,则目力受害不小;桌椅长短不合,削趾适履,则躯干受亏;其余类此者尚多,不能尽也。
然则为吾侪学者之计如之何?学校之设备,教师之教训,乃外的客观的也。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。夫内断于心,百体从令。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,我欲仁斯仁至,况于体育乎。苟自之不振,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,亦犹之乎不能受意也。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。
第四、体育之效
人者动物也,则动尚矣。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,则动必有道。然何贵乎此动邪?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?动以营生也,此浅言之也;动以卫国也,此大言之也。皆非本义。动也者,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。朱子主敬,陆子主静。静,静也;敬,非动也,亦静而已。老子曰无动为大。释氏务求寂静。静坐之法,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。近有因是子者,言静坐法,自诩其法之神,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。是或一道,然予未敢效之也。愚拙之见,天地盖惟有动而已。
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。前既言之,体育之效,则强筋骨也。愚昔尝闻,人之官骸肌络,及时而定,不复再可改易,大抵二十五岁以后,即一成无变。今乃知其不然。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: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,目不明可以明,耳不聪可以聪,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,事盖有必至者。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,今亦知其非是。盖生而强者,滥用其强,不戒于种种嗜欲,以渐戕贼其身,自谓天生好身手,得此已足,尚待锻炼?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。至于弱者,则恒自悯其身之下全,而惧其生之不永,兢业自持。于消极方面,则深戒嗜欲,不敢使有损失。于积极方面,则勤自锻炼,增益其所不能。久之遂变而为强矣。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,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。吾生而弱乎,或者夭之诱我以至于强,未可知也。东西著称之体育家,若美之罗斯福、德之孙棠、日本之嘉纳,皆以至弱之身,而得至强之效。又尝闻之,精神身体,不能并完。用思想之人,每歉于体;而体魄蛮健者,多缺于思。其说亦谬。此盖指薄志弱行之人,非所以概乎君子也。孔子七十二而死,未闻其身体不健;释迹往来传道,死年亦高;邪苏不幸以冤死;至于摩诃末,左持经典,右执利剑,征压一世。此皆古之所谓圣人,而最大之思想家也。今之伍秩庸先生,七十有余岁矣,自谓可至百余岁,彼亦用思想之人也;王湘绮死年七十余,而康健矍铄。为是说者,其何以解邪?总之,勤体育则强筋骨,强筋骨则体质可变,弱可转强,身心可以并完。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。
非第强筋骨也,又足以增知识。近人有言曰:文明其精神,野蛮其体魄。此言是也。欲文明其精神,先自野蛮其体魄。苟野蛮其体魄矣,则文明之精神随之。夫知识之事,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。于此有须于体者焉。直观则赖乎耳目,思索则赖乎脑筋,耳目脑筋之谓体,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。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。今世百科之学,无论学校独修,总须力能胜任。力能胜任者,体之强者也。不能胜任者,其弱者也。强弱分,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。
非第增知识也,又足以调感情。感情之于人,其力极大。古人以理性制之,故曰"主人翁常惺惺否",又曰"以理制心"。然理性出于心,心存乎体。常观罢弱之人,往往为感情所役,而无力以自拔;五官不全及肢体有缺者,多困于一偏之情,而理性不足以救之。故身体健全,感情斯正,可谓不易之理。以例言之:吾人遇某种不快之事,受其刺激,心神震荡,难于制止,苟加以严急之运动,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,而复使脑筋清明,效盖可立而待也。
非第调感情也,又足以强意志。体育之大效,盖尤在此矣。夫体育之主旨,武勇也。武勇之目,若猛烈,若不畏,若敢为,若耐久,皆意志之事。取例明之,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,又足以练习敢为。凡各种之运动,持续不改,皆有练习耐久之益。若长距离之赛跑,于耐久之练习尤著。夫力拔山气盖世,猛烈而已;不斩楼兰誓不还,不畏而已;化家为国,敢为而已;八年于外,三过其门而不入,耐久而已。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。意志也者,固人生事业之先躯也。
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,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,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。体育之效,至于强筋骨,因而增知识,因而调感情,因而强意志。筋骨者,吾人之身;知识、感情、意志者,吾人之心。身心皆适,是谓俱泰。故夫体育非他,养乎吾生、乐乎吾心而已。
第五、不好运动之原因
运动力体育之最要者。今之学者多不好运动,其原因盖有四焉:一则无自觉心也。一事之见于行为也,必先动其喜为此事之情,尤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知其所以然之智。明白周详知所以然者,即自觉心也。人多不知运动对于自己有如何之关系,或知其大略,亦未至于亲切严密之度。无以发其智,因无以动其情。夫能研究各种科学孜孜不倦者,以其关系于己者切也。今日不为,他日将无以谋生。而运动则无此自觉,此其咎由于自己不能深省者半,而教师不知所以开之亦占其半也。一则积习难返也。我国历来重文,羞齿短后,动有好汉不当兵之语。虽知运动当行之理,与各国运动致强之效,然旧观念之力尚强,其于新观念之运动,盖犹在迎拒参半之列。故不好运动,亦无怪其然。一则提倡不力也。此又有两种:其一,今之所称教育家,多不诺体育。自己不知体育,徒耳其名,亦从而体育之,所以出之也不诚,所以行之也无术,遂减学者研究之心。夫荡子而言自立,沉湎而言节饮,固无人信之矣。其次,教体操者多无学识,语言鄙俚,闻者塞耳。所知惟此一技,又未必精,日日相见者,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。夫徒有形式而无精意以贯注之者,其事不可一日存,而今之体操实如是。一则学者以运动力可羞也。以愚所考察,此实为不运动之大原因矣。夫衣裳襜襜、行止于于、瞻视舒徐而夷犹者,美好之态,而社会之所尚也。忽尔张臂露足,伸肢屈体,此何为者邪?宁非大可怪者邪?故有深知身体不可不运动,且甚思实行,竟不能实行者;有群行群止能运动,单独行动则不能者;有燕居私室能运动,稠人广众则不能者。一言蔽之,害羞之一念为之耳。四者皆不好运动之原因。第一与第四属于主观,改之在己;第二与第三属于客观,改之在人,君子求己,在人者听之可矣。
第六、运动之方法贵少
愚自伤体弱,因欲研究卫生之术。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。近今学校有体操、坊间有书册,冥心务泛,终难得益。盖此事不重言谈,重在实行,苟能实行,得一道半法已足,曾文正行临睡洗脚、食后千步之法,得益不少。有老者年八十犹康健,问之,曰:“吾惟不饱食耳。”今之体操,诸法樊陈,更仆尽之,宁止数十百种?巢林止于一枝,饮河止于满腹。吾人惟此身耳,惟此官骸藏络耳,虽百其法,不外欲使血脉流通。夫法之致其效者一,一法之效然,百法之效亦然,则余之九十九法可废也。目不两视而明,耳不两听而聪,筋骨之锻炼而百其方法,是扰之也。欲其有效,未见其能有效矣。夫应诸方之用,与锻一己之身者,不同。浪桥所以适于航海,持竿所以适于逾高,游戏宜乎小学,兵式宜乎中学以上,此应诸方之用者也。运动筋骸使血脉流通,此锻一己之身者也。应诸方之用者其法宜多,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。近之学者,多误此意,故其失有二:一则好运动者,以多为善,几欲一人之身,百般俱备,甚至无一益身者;一则不好运动者,见人之技艺多,吾所知者少,则绝弃之而不为,其宜多者不必善,务广而荒,又何贵乎?少者不必不善,虽一手一足之屈伸,苟以为常,亦有益焉。明乎此,而后体育始有进步可言矣。
第七、运动应注意之项
凡事皆宜有恒,运动亦然。有两人于此,其于运动也,一人时作时辍,一人到底不懈,则效不效必有分矣。运动而有恒,第一能生兴味。凡静者不能自动,必有所以动之者。动之无过于兴味。凡科学皆宜引起多方之兴味,而于运动尤然。人静处则甚逸,发动则甚劳,人恒好逸而恶劳,使无物焉以促之,则不足以移其势而变其好恶之心。而此兴味之起,由于日日运动不辍。最好于才起临睡行两次运动,裸体最善,次则薄衣,多衣甚碍事。日以为常,使此运动之观念,相连而不绝,今日之运动,承乎昨日之运动,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。每次不必久,三十分钟已足。如此自生一种之兴味焉。第二能生快乐。运动既久,成效大著,发生自己价值之念。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,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,心中无限快乐,亦缘有恒而得也。快乐与兴味有辨。兴味者运动之始,快乐者运动之终。兴味生于进行,快乐生于结果。二者自异。
有恒矣,而不用心,亦难有效。走马观花,虽日日观,犹无观也。心在鸿鹄,虽与俱学,勿若之矣。故运动有注全力之道焉。运动之时,心在运动,闲思杂虑,一切屏去,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,筋肉如何张弛,关节如何反复,呼吸如何出入。而运作按节,屈伸进退,皆一一踏实。朱子论主一无适,谓吃饭则想着吃饭,穿衣则想着穿衣。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,亦若是则已耳。
文明柔顺,君子之容。虽然,非所以语于运动也。运动宜蛮拙。骑突枪鸣十荡十决,喑噁颓山岳、叱咤变风云,力拔项王之山,勇贯由基之札,其道盖存乎蛮拙,而无与于纤巧之事。运动之进取宜蛮,蛮则气力雄,筋骨劲。运动之方法宜拙,拙则资守实,练习易。二者在初行运动之人为尤要。
运动所宜注意者三:有恒一也,注全力二也,蛮拙三也。他所当注意者尚多。举其要者如此。
秋水片帆明似箭。又映带烟峦葱茜。有垂钓任公,鸣筝挟瑟开芳宴。
还共举,梨花盏。
质崚嶒,气清远。泛玻瓈、鹧鸪斑擅。拚一饮香浮,醉中海国壶中选。
应胜似,涪阳篆。
时为嘉禾小倅,以病眠,不赴府会。
水调数声持酒听,午醉醒来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几时回?临晚镜,伤流景,往事后期空记省。
沙上并禽池上暝,云破月来花弄影。重重帘幕密遮灯,风不定,人初静,明日落红应满径。
七步周行浑属我,不妨闲唱太平歌。
灵利汉,不消多,法门广大遍周沙。
若能当处分明了,只在如今一刹那。
莫求真,休觅假,真假中间都放下。
晃晃威光烁太虚,不知谁是知音者。
赞不欣,徒说谤,三际无心俱扫荡。
正体堂堂一物无,是佛是魔俱一棒。
小根闻说暗攒眉,绳上生虵又更疑。
拨转面前关棙子,只许当人独自知。
阿呵呵,大圆觉,流出菩提遍寥廓。
鬼面神头几百般,无瑕镜里皆消却。
君不见觌面相逢机掣电,
直饶天眼不能观,点著不来真死汉。
劝君参,参彻灵明自己禅。
善财不用南方去,黑白分明在目前。
劝君信,信心战退魔军阵。
此是华严最上乘,森罗万象皆相应。
劝君修,六门通达任优游。
寒山拾得才相见,指点丰干哂未休。
火风催,四山逼,那时要见君端的。
有个真空解脱门,千眼大悲何处觅。
有时放,有时收,唯有知音暗点头。
杏华村里如相见,跳出沩山水牯牛。
有时喜,有时嗔,无位真人迸面门。
殷勤为说西来意,暮楼钟鼓月黄昏。
有时唱,有时歌,颠言倒语不奈何。
声声尽出孃生口,不属宫商一任他。
有时默,有时笑,懵懂铁鎚无孔窍。
轻轻触著便无明,只这无明元是道。
有时行,有时坐,露影藏身成两个。
不独张三会打油,细观李四能推磨。
无缝塔,见无因,巍巍本自隐深云。
国师样子应难造,不觉锋棱露一层。
无底钵,手中擎,百千沙界里头盛。
大庾岭头提不起,都缘著力太多生。
没底船,不曾漏,千里雪浪皆能透。
只凭一个把稍人,谁管狂风连地吼。
无鑐鏁,孰安排,鏁断重关绝往来。
巨灵抬手空劳力,唯有无心便得开。
无毫拂,是何物,击碎狐疑山鬼屈。
一喝唯言三日聋,谁怜大辩翻成讷。
无孔笛,最难吹,角徵宫商和不齐。
有时品起无生曲,截断行云不敢飞。
无根树,直侵云,枝条郁密盖乾坤。
劫火洞然烧不得,利刀斩处亦无痕。
无面目,担板汉,玩水游山无侣伴。
迦叶门前倒刹竿,文殊剑上全身现。
日面佛,乾屎橛,八两半斤谁辨别。
七斤衫子恰相当,镇州休更秤萝蔔。
野鸭飞,鸾对舞,三个孩儿抱华鼓。
赵老曾看半藏经,灵云一见桃华悟。
真实语,报君知,不用思量不用疑。
春来决定千华秀,冬尽长天片雪飞。
头头漏泄真消息,那个休心辨端的。
眼横鼻直一般般,不离当处休寻觅。
古佛言,祖师说,千圣路头同一舌。
他日人天匝地来,那时方表而今决。
居家不能乐,忽忽思中原。
慨然弃乡庐,劫劫道路间。
穷山多虎狼,行路非不难。
昔者倦奔走,闭门事耕田。
蚕谷聊自给,如此已十年。
缅怀当今人,草草无复闲。
坚卧固不起,芒背实在肩。
布衣与肉食,幸可交口言。
默默不以告,未可遽罪愆。
驱车入京洛,藩镇皆达官。
长安逢傅侯,愿得说肺肝。
贫贱吾老矣,不复苦自叹。
富贵不足爱,浮云过长天。
中怀邈有念,惝怳难自论。
世俗不见信,排斥仅得存。
昨者东入秦,大麦黄满田。
秦民可无饥,为君喜不眠。
禁军几千万,仰此填其咽。
西蕃久不反,老贼非常然。
士饱可以战,吾宁为之先。
傅侯君在西,天子忧东藩。
烽火尚未灭,何策安西边。
傅侯君谓何,明日将东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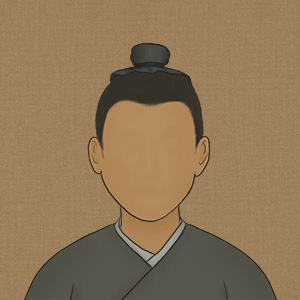 毛泽东
毛泽东 陆游
陆游 强至
强至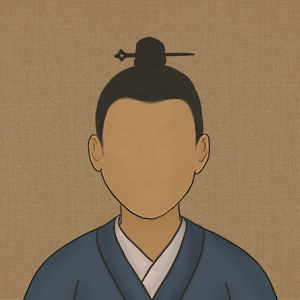 尹廷高
尹廷高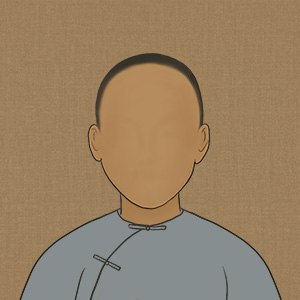 董元恺
董元恺 张先
张先 葛立方
葛立方 释道川
释道川 吴芾
吴芾 苏洵
苏洵